他的心在田野 ——缅怀我的老师刘绪先生(组图)
发布时间:2022-02-17 17:21 |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17日 11版 | 查看:813次

2003年11月,本文作者(左二)随刘绪(右)在周原指导本科生考古实习。

2016年4月,刘绪在安阳博物馆考察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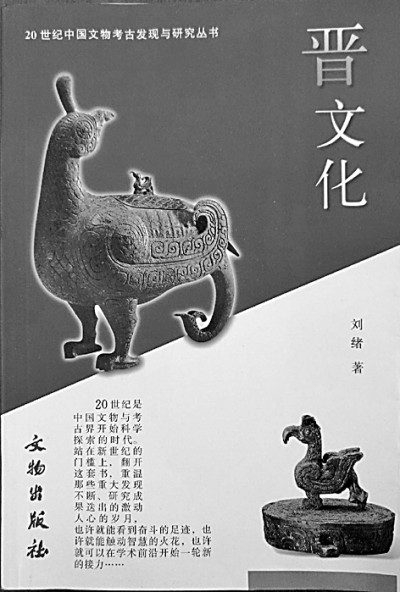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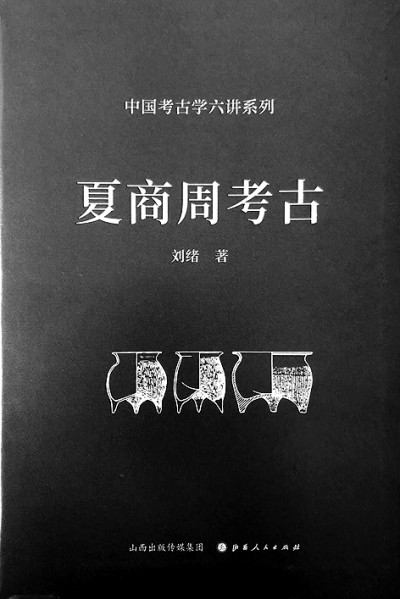

2007年7月,刘绪在发掘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述往】
学人小传
刘绪(1949—2021),山西广灵人,考古学家。197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生前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或参加过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著有《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等。
我的老师刘绪先生逝世已经四个多月了,每念及此,常常精神恍惚,枯坐良久,思绪纷纷,提笔属文却不知从何说起。
2021年9月26日0时43分,刘绪老师于北医三院病逝。直到当日傍晚,我才得知这个噩耗。其时,我正在校外参加活动,头脑中瞬时一片空白,周围一切仿佛与我失去了关系。虽然老师已患病住院两年,我心里或多或少有点准备,但当噩耗传来,还是不能接受。我呆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告退出门,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27日一早,我赶往北医三院和老师告别。沿着北医三院太平间窄窄的斜坡扶棺而上,悲伤之情再也无法抑制。灵车先载他回北大,众多师生肃立在西门外为他送行。在殡仪馆,闻讯赶来的师生一一与他告别。师母乔老师在他的骨灰盒边放下一柄手铲,那是考古学家的象征。从1972年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算起,刘绪老师心系考古50年,一手拿粉笔,教书育人,一手握手铲,考古夏商周,一生功业尽在于此。
一
我跟随刘绪老师读书的时间比较晚。1999年,受同学鼓励,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所幸通过了笔试,复试时才第一次见到刘老师。
刘绪老师身形瘦削,目光专注,炯炯有神,讲话时,两眼尤其生动。他让我谈谈某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还让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他的声音不高,温润柔和,略带一点晋北口音。我把有关那个问题的不同观点陈述一番,至于自己的看法,则支支吾吾,完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他笑了笑说,能了解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基本材料还不是很熟悉,没有深入,当然就不会有看法。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的状态点透了:为了应付考试记住了很多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如果不吃透原始材料,找到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看法的。这大概可以算是刘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吧。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刘绪老师安排我到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发掘。这次发掘是基于“祖乙迁邢”的课题,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北省文研所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临行前,刘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参加发掘的有中国社科院的牛世山、河北省所的段宏振,他们二位做过很多田野工作,经验丰富,到了工地要多向他们请教,遇到困难要及时反馈。我从北京出发,到石家庄稍作停留,随后就赶赴邢台东先贤。我们租了村里一个大院子,开始了正式发掘。
过了月余,刘老师来到工地。事有凑巧,我那几日正对探方里刚刚出现的一片遗迹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处置。刘老师下到探方,拿起手铲刮土,询问相关情况。他判断,这很可能是刚刚冒头的一座陶窑。随后的清理果然证实了这个看法。他教导我,在判断遗迹性质的时候,不能孤立看待遗迹现象,要注意平剖面的结合,既要根据已出现的遗迹现象,也要和周围的遗迹联系,还要对相关的遗迹有直观的认识,比如一座陶窑要有操作间、火门、窑床或者窑箅、出烟孔等,这样的发掘才能清楚完整。
本来安排刘绪老师到邢台市区休息,可是他坚持和我们一起住在乡下,说这样交流更方便。于是,刘老师和段宏振、牛世山住在里间,我和河北省所的同志住在外间。发掘出的陶片都摆放在院子里,每天吃完午饭,刘老师就带我看陶片。刘老师摸陶片、识陶片的功夫在考古界是众所周知的。每每遇到有典型特征的口沿、器底或者纹饰,他就给我细细讲解。随后几天,刘老师又带着我们在邢台周围做田野调查,了解相关遗址的情况,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是刘老师第一次对我进行田野指导,提升了我对田野考古的认识和理解。
发掘显示,东先贤遗址包含了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为“祖乙迁邢”的说法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我们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跟随刘绪老师读完硕士、博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离北大不远,所以经常回学校和刘老师聊天。到了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时候,北大西门外还有一些小饭店,经常是师徒二人一人一碗面,后来也常去校内的畅春园食堂和勺园。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谈考古新发现,有时谈我的工作生活。他也经常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新发现的问题,嘱我回去仔细整理写出论文。
2019年9月,刘绪老师确诊肺癌。我只在他第一次化疗之后的某一天,得以陪床一日。上午输液,刘老师闭目养神,偶尔谈话,主要讲的是前段时间考察几处考古工地的情况。住院之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考古发掘现场,那时他的胸部已偶尔疼痛,但他依旧没有离开工地。近来我时常想,如果他提早一点去医院治疗,这个病能不能治愈呢?毕竟,我认识好几位肺癌患者,后来都痊愈了。
那天下午,他专门谈了三代都邑考古问题,指出种种现象和变化,命我回去整理成文。他还告诉我,趁着化疗之前的几天时间,他在病床上赶出了一篇序文,“已经答应人家了,化疗以后不知道啥情况,耽误了不好”。
二
刘绪老师常说,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也是考古学的生命力所在,不做田野就成不了真正的考古学家。50年来,全国很多考古工地,都留下了他瘦削的身影。
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时,刘绪老师就参加了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他当年的工作日记和探访记录如今就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陈列着,这是对考古学家最好的纪念。本科毕业后,他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又参与发掘了大同方山永固陵、夏县东下冯、沁水下川等遗址。
1980年,他考取邹衡先生的研究生,回到北大,从此之后,几乎每年都跑田野,多则半年,少则几个月。
入学不久,邹衡先生便派他去山西曲村参加发掘。留校工作后,他又以辅导老师的身份,在曲村遗址带学生实习。曲村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考古遗址,前前后后将近20年,正是在曲村,他培养了一批从事田野考古的学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绪老师开始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这是一处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也是邹衡先生拼命保护下来的遗址。多年的发掘工作,使他对琉璃河遗址充满感情。2018年,琉璃河考古重新开展,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琉璃河工地,一方面指导新的发掘,一方面整理发掘资料。在罹患重病的最后两年里,他利用放疗化疗间隙,完成了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报告的初稿。2021年12月19日,刘绪老师去世两个多月后,在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中,几代考古人回忆起刘绪老师在琉璃河的考古活动,与他共事多年的北京考古所赵福生先生泪洒直播间。
从20世纪末开始,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刘绪老师又先后参与了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2012年退休时,他以为田野工作会减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变多,计划将自己多年考古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但是,每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们带队田野实习,总是希望刘老师能去做辅导教学。有他在工地上,他们心里才踏实。地方上的考古队同人,听说刘老师退休了,也纷纷在工地发掘或整理期间,请他去指导。如此一来,原本的退休计划很快就泡了汤,他仍然奔波于考古工地,甚至比以前还要忙。
刘绪老师早年的生活很艰苦,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胃病。20世纪70年代在发掘方山永固陵期间,就曾病倒在工地上。在天马—曲村、琉璃河、周公庙等考古工地上,他也不止一次生病。只要身体稍好,他就立刻回到工地,辅导学生,解难答疑。
刘绪老师说,这么多年,只有一次,他动摇过。那是在曲村考古工地,徐天进老师正在发掘的墓葬突然塌方,徐老师被深埋在地下,20多分钟后才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刘老师当时情绪低落,在回宿舍取徐老师的换洗衣物时,脑子里闪现过退出的念头。徐老师获救后,刘老师又和过去一样投入田野工作之中。
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使得刘绪老师对田野考古现象的判断准确率非常高。按照他的指导进行发掘,通常不会造成发掘破坏。他也熟稔相关考古资料,对新材料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准确深刻。在考察发掘现场,他会把自己的看法无私地告诉工地负责人,帮助他们分析资料,解决难题,顺利地编写考古报告。
他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考古,他的一生与考古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心永远在田野。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考古现场,但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的考古发掘。他不止一次对夫人说,我又梦见去考古了。琉璃河、周原、盘龙城、天马—曲村、方山二陵……他一生去过太多的遗址,最舍不得他的考古事业。
三
有学者说,刘绪老师是夏商周考古的“活字典”。此言不虚。
夏商周的时间跨度较长,内容异常庞杂,能够贯通夏商周的学者并不多见。刘绪老师对于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研究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几乎在所有重大学术问题上,他(刘绪)都有深刻的分析和真知灼见”。
在邹衡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是刘绪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成名作,堪称考古学论文的典范。这篇论文从考古发掘资料入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宏观问题,在考古学上夯实了夏与先商并行发展的考古学根基。这篇论文也奠定了此后刘老师研究夏文化、先商文化和商文化问题的基础,其结论时至今日仍可成立,并被最近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刘绪老师的夏文化研究独树一帜,对于夏文化的年代、分布、类型,早期夏文化,夏商文化的分界等问题都有阐述。他生活中待人随和,但在学术研究中却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比如,对夏文化研究的现状,他尖锐地指出,看似热闹,实则是虚火。再如,他的论文《偃师商城——不准确的界标》是对偃师商城夏商分界唯一界标说的一次驳议,发表后果然引起争议,他随后又发表《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的若干问题》《夏末商初都邑分析之一——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比较》等系列论文,将夏商文化分界问题引向深入,这些论文已成为关于夏文化、商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
刘绪老师对商文化有全面研究,对商族先公的迁徙与商文化的起源、商文化的分布、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商城的性质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河南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现之初,他通过对考古材料和传统文献的梳理,提出了洹北商城可能为河亶甲城,发表了论文《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一年之后在该遗址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城,尽管目前关于这座商城的性质还在讨论之中,有学者认为是盘庚迁殷,但河亶甲相都之说仍不可完全排除。
由于多年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刘绪老师在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对先周文化、周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等都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除了收集在《夏商周考古探研》和《夏商周考古》两本专著中的论文之外,他还应邀撰写了《晋文化》这本关于晋与三晋考古的集大成著作。可惜,由于体例限制,出版时有很多内容被删减了,但这些内容都保存在他的课堂讲义中。再如《周代墓地族系分析》一文,是刘老师关注多年的重要课题,对于周代墓葬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还探讨了周代族群的分布、殷遗民、周代的怀柔统治策略等社会历史问题,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上都有示范意义。
刘绪老师治学重勤。他在考古工地发掘或考察时,对于特殊或重要现象,随时记录,或绘下草图,若当时忙于工作,也会在事后进行补记。1976年参加的方山二陵的调查和发掘,是特殊年代的一次艰苦发掘,但他还是尽可能做好田野工作,并查阅了大量文献,做了非常详实的工作笔记。多年以后,他对方山二陵的发掘还依依不能忘怀,撰写了《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一文,纪念一段无法割舍的记忆。
刘绪老师治学善思。他对夏商周考古积淀日久,许多问题沉潜在脑海中,在考察或阅读时遇到材料,往往可以融会贯通,提出新解。“当看到泜水流域元氏县出土铸有地名‘軧’和‘軧侯’的西周早期铜器铭文时,马上想到可能与昭明之居的‘砥石’有关,遂写一短文《昭明之居与元氏铜器》”,正是夫子自道,授人以渔。
刘绪老师治学求实。他的文章立论扎实,从不空发议论,也反对不切实际的猜想。他的三篇专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长文,《夏与夏文化探讨》《商文化的纵横考察》《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都是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论文。有学者评价,刘绪老师的论文行文虽平实,但极耐读,几乎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刘绪老师一贯主张,从事三代考古一定要夏商周贯通,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在《谈一个与早期文明有关的问题》中,他对周代以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进行了梳理,从一个长时段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一次示范性研究。在专注夏商周的同时,他认为还有必要上联新石器时代、下接秦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在回忆刘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刘绪先生专业是夏商周考古,却对新石器、秦汉熟稔在心”,可谓知音之论。
刘绪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三部著作,还有他参加编写的关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周原遗址、琉璃河遗址等考古报告,这些都是夏商周考古学的宝贵财富。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哀悼刘绪老师的挽联概括得很恰当:
学如海、术比地、教似天,终生耕耘为考古;
夏文化、商文明、周王朝,一心探研修国史。
四
刘绪老师在北京大学工作近40年,教书育人,重在言传身教,有口皆碑。他常说“本人生性保守,凡讲课必须备有讲稿,这样心里才比较踏实”。他的讲稿,几乎年年都会增补新的内容。他的课,全面、系统而有深度,听讲者无不收获满满。他讲课时,与平时谈话稍有不同,声音抑扬顿挫,表情到位,声情并茂,颇受学生欢迎,每每有外校学生慕名前来旁听。
刘绪老师性格温和,待人随和,颇易接触。无论在田野,还是在燕园课堂,学生们有学术或者生活上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量抽出时间一一接待。在退休之前,他的办公室在博物馆209室,经常有学生前来咨询,谈完事,他还要亲自把来访者送出办公室,挥手告别。
他的心中经常挂念学生,不仅是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多年的学生。在生病治疗的两年里,他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偶然发现过去学生考古实习的资料,就拍个照发给他们,留作纪念。每个收到照片的同学,都会感到无限温暖。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比较紧张,他比我还焦急。我工作多年都没有买房,他又是很着急,甚至要借我一部分钱作首付款。在我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刘绪老师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生病住院期间,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劝阻朋友、学生们的探视。偶尔有人来探视,他常常因为无法亲自送客而满脸歉意。
刘绪老师不止一次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是要特别感谢他的恩师邹衡先生。在曲村工地,从考古发掘到室内整理的各个环节,邹衡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辅导他。邹衡先生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在学界,他的要求严格也是出了名的,正是如此,刘老师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刘老师也被誉为邹门弟子中,深得邹衡先生真传的学者。
刘绪老师一生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对邹衡先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到曲村工地库房整理资料。夏天酷热难耐,因经费紧张,邹衡先生嫌电扇太贵,不同意买。有一次,刘老师去西安出差,看到有稍微便宜的电扇,就自费买了一个,从西安背回了曲村,安放在邹衡先生整理资料的库房里。在80年代至90年代,刘老师还协助邹衡先生完成了《天马—曲村》考古报告的编写,并执笔完成了周代居址部分。邹衡先生去世后,刘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若不从先生学,无先生培育与提携,当然也无今日之我。如果说自己专业有所长进,学业感觉充实,则首先有赖于先生,得益于先生,对此我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刘绪老师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怀有同样的敬重之情。退休之后,他接受了整理苏秉琦先生讲义、遗稿的工作。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他认真细致地整理一包一包的材料,出版了苏秉琦先生遗稿《战国秦汉考古》《另一个三叠层》。他说:“苏先生是我的老师,整理苏先生的遗稿,我责无旁贷。”
刘绪老师性格平和,与人为善,但内心也有刚正的一面。他曾对我讲过某单位评聘博导,连续两年邀请他为外审专家,评审的都是同一位学者。他认为这是一位当前非常活跃、卓有成就的学者,不仅在该单位,即便在国内,也是专业内的佼佼者,晋升应无问题,就很认真地填写了推荐意见。可惜连续两年,这位学者都名落孙山。他感到事情很奇怪,也很生气。第三年,当该单位又联系他做外审专家时,刘老师没有答应。他说,这样的评审明显跟学术无关,我可不愿意配合他们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刘绪老师对生活充满热爱,即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时常把他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大家。他会在散步时,捡起几片树叶,摆成正在舞蹈的人形,拍照发给大家。那个舞者身形婀娜,动感十足,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他多才多艺,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娴于多种乐器,工于书画,年轻时的画作在家乡获得极高赞誉。他的外甥曾说,如果舅舅不从事考古研究,或许现在就是著名的画家了。在他全身心投入考古工作之后,还保留着篆刻的爱好,在赠送友人的著作上就钤印着他自制的名章。
刘绪老师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精神魅力,凡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感到如沐春风,或许可称为君子之风。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刘老师庶几当之。
如今,老师已去,夜半惊醒,唯有泪滑落。所幸老师的著作还在,老师的考古事业还在,我辈唯当发奋,不负老师的教导和培养。
(作者:张明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