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在上海,那段因患“甲肝”被隔离的日子(组图)
发布时间:2020-02-04 11:31 |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2-03 16:27 | 查看:1190次
原创孔娘子厨房孔娘子厨房
这是一篇我写在2005年发表在《现代家庭》杂志上的文章,之所以又翻出来看,是因为看到“上观”公众号上那篇“31年前,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甲肝,我们是这样战胜它的”回顾报道,32年前我的亲身经历也曾那么苦涩。
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的形势仍然严峻,回顾是防止我们太悲观,因为事过之后,也许在此一疫中我们都会留下一些值得珍惜的片段。
在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一段珍贵的日子,整个属于黄色。
1988年,上海曾经历一场“甲型肝炎”流行的恐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班回家,路过新村的菜摊,看见有毛蚶卖,兴奋地买回家洗净,用开水一烫,就和同样嗜海鲜的老公大吃起来。我的女儿3岁,不好好吃饭在地下跑,我拿了毛蚶肉追她,硬塞到她嘴巴里,被她一再吐出来。

只隔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突然上吐下泻,老公抱着女儿扶着我去医院打点滴,然后把我送到妈妈那儿,他抱了女儿去奶奶家。泻到第二天,我人不行了,随妈妈去地段医院看病,突然在门口软下来,连门槛也跨不过去。这时,整个上海已经发现了多起“甲肝”,一检查,我也被判患了“流行性甲肝”。
随着甲肝患者人数呈几何式增长,传染病毒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像被机关枪扫射似的一排排倒下来,医院人满为患,恐怖情绪弥漫了整个上海。我被隔离在妈妈家的亭子间,全身乏力,眼睛蜡黄。妈妈跑上跑下帮我煮猪肝汤,鲫鱼汤。像送牢饭一样,放在门口让我拿进去吃。楼上还有哥哥一家,我不敢出门,除了用那里的厕所。
哥哥很紧张,听见我上楼耳朵就竖起来,我一离开马桶,他就跑过来消毒。一天我软弱地靠着墙壁移上楼,哥哥发火了,让我身体腾空,因为他的小女儿喜欢摸墙壁的。回到亭子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我是很惭愧,嫁也嫁出去了,生病了还要回家麻烦妈妈,连累哥哥。我更是想念我的女儿,想念老公。
可是老公为什么不来看我呢?女儿呢,在奶奶家会不会整天哭?家里没有电话,我干巴巴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没有人说话,没有书看,感到很委屈。一天,突然我听到楼下电话间阿姨叫我的名字,妈妈赶紧跑下去帮我听,回来惊慌地告诉我,你老公也得了甲肝,被隔离到浦东自己的家了!现在好,一家人分三个地方!妈妈累得气喘吁吁,她一向是个享福人,现在为了我,连脚底板都走痛了。
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只沮丧了一会儿,小学数学里学的“合并同类项”“嘟”地一下从头脑中冒出来,黄黄的脸上露出欣喜。我翻身坐起来,对妈妈说,我要回浦东去,和老公会合,反正两个人是同一种传染病,要死要活都要在一起。看着妈妈很犹豫也很疲惫的神情,我更坚定了回去的念头。
妈妈无奈,怕我路上撑不住,便拿出钱来,叫我坐出租车回家。那时的出租车司机和电话间、商店里的人一样,看见有人脸色黄,便要起疑心,不敢为他服务,连他的钞票都不敢要。大街上,到处弥漫着酒精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把自己包装了一下,表面很镇静地跳上一辆出租车。大气不敢出地回到浦东。老公没有料到有人会“探监”,出来开门的时候一脸惶惑。见到是我,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一看,这哪里还是我以往面皮白皙的老公,整张脸黄得像一张腊光纸,眼白也是黄的,再一笑,相当可怕。
老公说,自己发烧好几天,也没有人端水给他,憋了几天,才戴了帽子和口罩去公用电话间给我通风报讯的,打完电话被旁边一个女人瞥见腊黄眼珠子,那女人怪叫一声,像见了鬼似的,他连忙逃走。老公夸我聪明,和他心通,能回来和他同甘共苦。我抱着他哭了,责怪自己不好,把病毒传染给他。
老公说,你也太孤陋寡闻了,有关方面已经调查出来,我们都是被污染的毛蚶害的。你知道那几船被甲肝病人的粪便污染的毛蚶害了上海多少人吗?三十多万!此事已因发病人数之多、影响之深、经济损失之重而震惊世界。
我们两个甲肝病人,不幸而又有幸,关在浦东新村的房间里,除了吃就是睡,如果没有一台电视机,仿佛与世隔绝。我们体质很弱,说不了很多话就会昏昏睡去,爬起来煮点粥吃些酱菜,再睡。有时我早醒来,就着阳光侧脸看着老公。自从结婚生孩子以后,每天忙忙碌碌往返黄浦江两岸,送孩子,上班,买菜、烧饭,免不了为了一些琐事拌嘴,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长久地看他的脸,抚摸他。
老公醒来了,微笑着说,怎么样?有力气啦?要听医生的话,女儿还等着我们早点去接她呢。我笑了,我们乖乖地手拉手看天花板,称赞女儿的精怪,想象着如果那天她被我逼迫,吃下那有毒毛蚶,后果不可设想。而三岁的女儿如果得病有个三长两短,我做妈妈的跳进黄浦江也赎不了罪了。
甲肝病人从发病到恢复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那一个月中,我们无人打扰,偶尔出去买点菜,也不敢多去公用电话间,怕招人嫌。在深居简出的日子里,我老公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入学通知书,开学在即,他更迫切希望GPT指标降下来,脸上的黄疸褪去,可以顺利过关。可是越急越不行,一个多月以后,我拿到合格的化验单,可以解禁了,而他的指标仍然没有合格。
我实在等不了他了,决定独自去看望女儿,把女儿抱到妈妈那儿去,让她奶奶休息。老公耍赖,像孩子一样,一定要跟着我去看女儿。我让他发誓决不碰孩子,也不跟她说话,只是隔三步路看看而已。
我穿了一套新衣服喜气洋洋的,老公理屈辞穷、偷偷摸摸似地跟着我来到复兴路奶奶家。天哪,一个月不见,女儿妞妞长大很多,梳了小辫子倚在大门上吃香蕉。我弯下身来对她说:“妞妞,叫我呀!”想不到妞妞的眼珠骨溜溜转了很久,竟然叫了我一声“阿姨”!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抱起她说,我是妈妈呀,我是妈妈呀,妞妞怎么连妈妈也不认识啦。怎么搞的啦!
我一点也没有察觉,这时妞妞的奶奶已经不高兴了,她吃辛吃苦带了孩子一个多月,我见面连一句好话也没有给她说,反而像女儿受到虐待似的痛哭流涕。我老公机灵,连忙跨前一步对他妈妈说好话,并使劲向我使眼色。我们不能一起在奶奶家吃饭,我像捡到失而复得的宝贝,要抱女儿走了,这时老公显出缠绵来。
有孩子的女人就是这样奇怪,前几天还和他好得像新婚,见到孩子就把老公完全忘记。我忘了他接下去又要被关到浦东孤零零地生活,直到GPT检验出来正常。老公很有涵养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公园走一走,那里空气流通。好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复兴公园,老公和我们母女隔着三步路的距离,像一个陌生叔叔似的和妞妞搭话,讨好她,而一有接近女儿的迹象就被我大喝一声。
终于我带着妞妞回到妈妈那里,想住几天。但是想不到家里居然多了个半岁的小毛头,原来我嫂子也得了甲肝,而我哥哥远在日本。妈妈忙得一塌糊涂,没有留我,现在我也忘记了结果是和女儿流浪到哪里去了……
1988年那一场流行性甲肝带给我一片混乱的回忆,在这片混乱的黄色中,惟有一段湖面般平静的日子是美丽的,那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美丽种在我的心里。以后,每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来临,我就想,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两个人。不,还有妞妞,我们有三个人!
1988年上海这场甲肝流行,31余万人感染,死亡47人。
我老公在GPT指标正常以后,马上飞赴日本,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写于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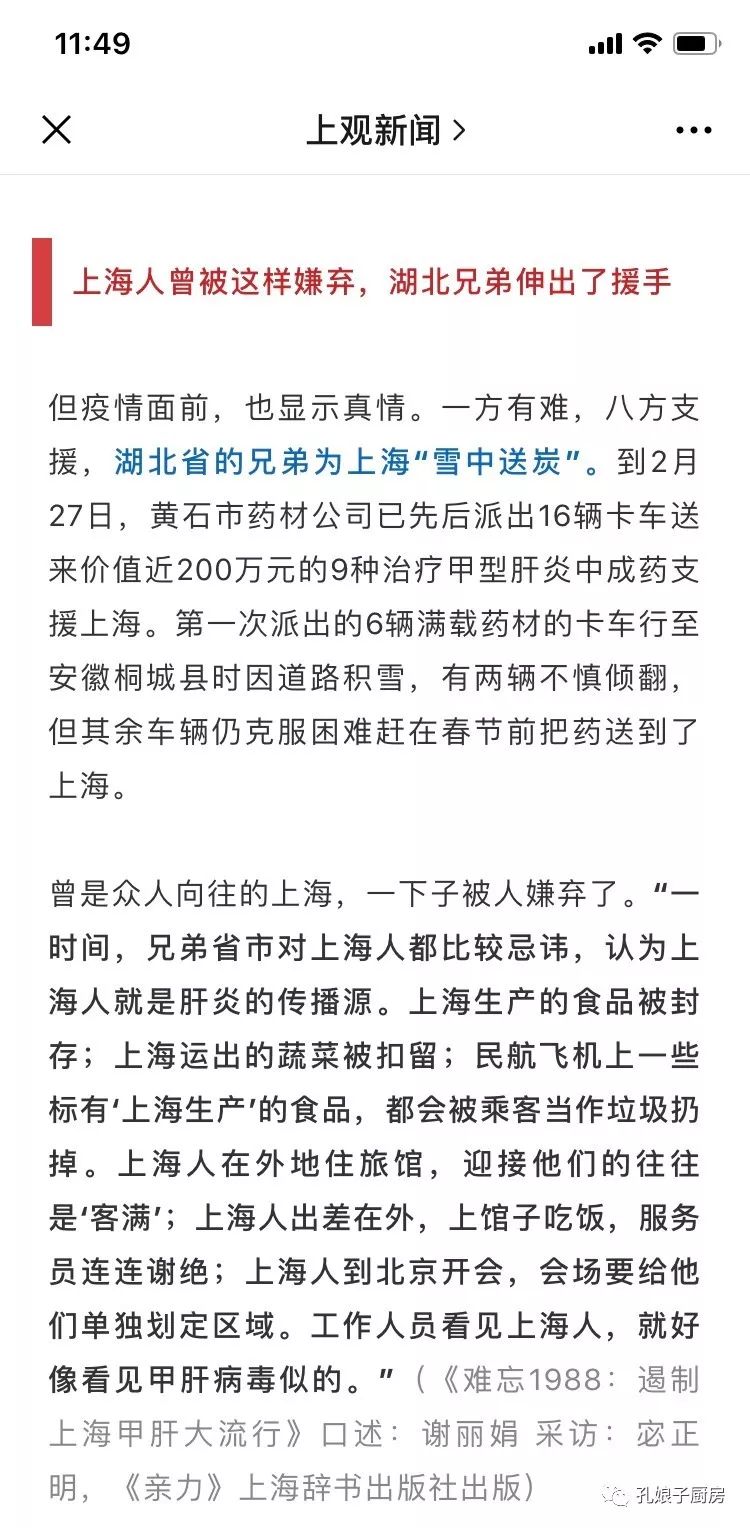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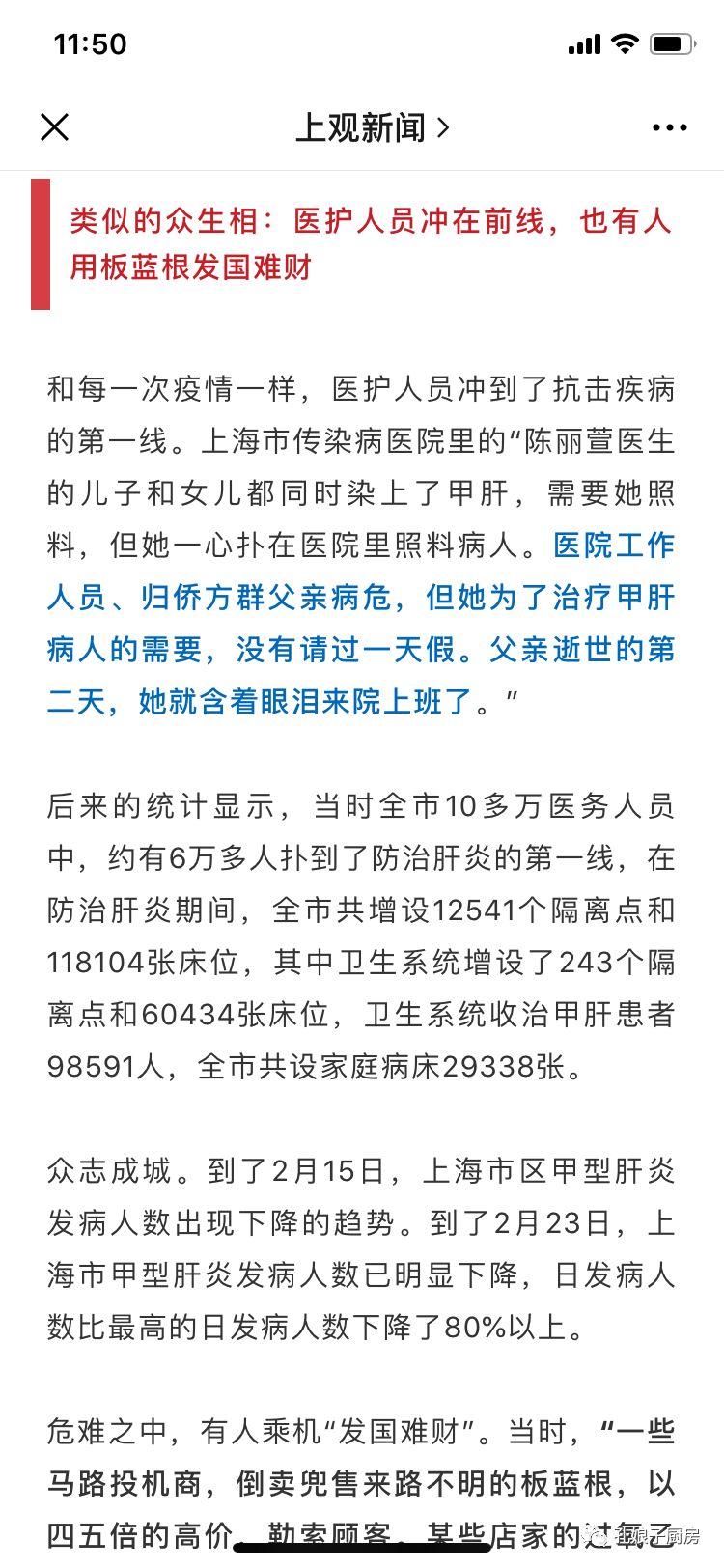
以上是上观公众号上的文章图片,文章在腾讯上的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00202A04ROE00

原标题:《32年前在上海,那段因患“甲肝”被隔离的日子 | 孔明珠》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