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的电影恨过的导演(图)
发布时间:2019-03-21 11:04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9年03月18日 第B02版 | 查看:84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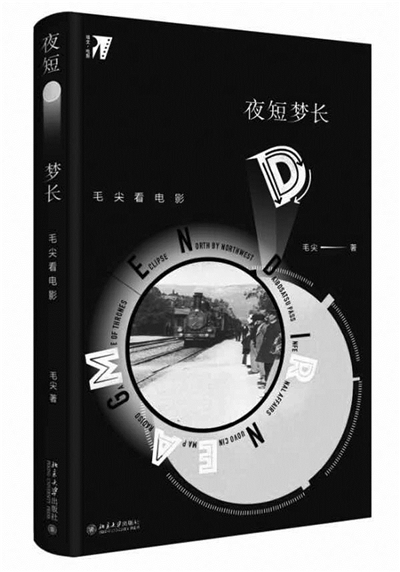
主题:《夜短梦长》新书分享会
时间:2019年3月9日14:00
地点: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嘉宾:格 非 作家、清华大学教授
毛 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夜短梦长》作者
主持:吴觉人 资深选片人、影评人
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
人生中不经意触碰到一些电影从此打开对电影、生活或是其他思想方面的维度
主持人:从《非常罪非常美》开始,毛尖老师这么多年来有关电影的写作、批评一直笔耕不断。她的文字带给我们关于电影的思考和品味,特别有趣。这次正好借《夜短梦长》的出版,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究她是如何写作这些电影的。格非老师也是对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等各方面有着很深刻的涉猎。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会不经意间触碰到一些电影,它们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从此打开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电影、对于生活,或是其他思想方面的维度。想问两位老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电影曾经给你们带来过这样的触动?
毛尖:我大学一年级就很有幸上了格非老师和宋琳老师的写作课。格非老师给我们讲过的很多名著和电影给我们开了光。在我们只知道奥斯卡的年代,他给我们讲了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讲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和《呼喊与细雨》。虽然跟现在你们的见识没法比,但是回头看,在我们的十八岁,二三十年前在舞会、聚会中和别人说起《芬妮和亚历山大》,那就是很酷了。
那个时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恰巧碰上读书热、哲学热,现代主义、现代派热,所以,我们非常热衷于追索一些看不懂的电影,越看不懂越觉得厉害。这样的状况对于我自己,大概持续了有15年。那一段时间,只要谁说“这个电影难懂”,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想找来看。找不到就去图书馆找相关介绍和评论看。
1997年,我到香港读博士,传说中的经典电影、烧脑电影,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真的有点眩晕。香港三年,我真是没好好读自己的专业,我导师是做古典文学的,但我披星戴月地把资料馆的经典电影差不多都看了,自修了一个电影专业的本科加硕士课程。我毕业的时候去跟音像资料馆老师告别,他扎着一根小辫子,很动情地说,你是我们这个馆接待次数最多的人。自己后来傲娇地想,我这种看电影、写电影的方式,跟新浪潮时候那批人还挺像的,特吕弗不就这样吗?
然后,2000年回到上海,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我自己有一个剧烈的左转,师友的影响是一方面,当时周围很多朋友转向文化研究;时代氛围的变化是另一个方面。大概有一两年时间,我只看国产电影,一边把共和国的很多电影又复习了一遍,把少年时代的一些电影线索重新捡了回来。比如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是《柳堡的故事》,王苹导演的,副班长和二妹子好上了,不用接吻,不用拥抱,镜头表现一下风车转、河水流淌,你就知道他们心心相印了,一整个世界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电影的风景抒情能力太太强大了。
如此,因为共和国电影,又去看了很多苏联电影。发现苏联电影的语法原来已经这么高级了,很激动。看爱森斯坦、看杜甫仁科,看杜甫仁科的《大地》特别感动,黑白片,却有彩色的效果,里面有果园镜头,拍出的苹果鲜艳多汁,比彩色胶卷的效果还好还饱满,这是苏联的镜头。还有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还有七个小时的《战争与和平》。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就是《战争与和平》,没有之一,比好莱坞的《战争与和平》强太多。
如此回头看看,我一开始是对美国电影感兴趣,然后看欧洲电影,然后转到对社会主义电影感兴趣,又回头再去看西方。
因为电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里跋涉
毛尖:中间还有一点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就是电视剧对我的影响。1997年《雍正王朝》播出,让我开始成为电视剧观众。之前我们从海外带电影回大陆,《雍正王朝》开始,我们带国内的电视剧给香港朋友看。然后到《暗算》《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出来,自豪感猛涨,感觉“国产电视剧”也终于出人头地了。为此,我还在文汇报开了电视剧专栏,十多年了,虽说浪费了很多时间看烂剧,但对我自己的影响真是非常大。之前我们聊天,格非老师也说我用那么多时间看了那么多烂片,但是我安慰自己一下,看过的烂片也不会全部破烂掉吧,还是有一些东西留下来会结出奇怪的果子。
不过真的也是,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时我会想起伯格曼的一句话,“我一直到58岁才走出青春期”。他对自己青春期的定义非常悲惨,“一个漫长又灾难的青春期”。我当然不是说自己的青春期也如此恐怖,而是说,因为电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里跋涉。常常,看西方电影跃入西方电影的青春期;看苏联电影,又好像把苏联的青春感同身受一遍。这个经验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候确实有非常悲伤的感觉。
格非:毛尖刚才说我当年教过她写作课,那是1988年。毛尖这本叫《夜短梦长》,我就首先从两个部分说起,一个是“梦”,一个是“夜”。
电影从根本来说,就是布努埃尔当年说的,“电影是一个伟大的梦幻”。它吸引我的并不是我从电影里面了解到什么事情,不一定。很多电影我们看过十几遍照样看得下去,它是在帮我们做梦,反映的是我们自身的欲望。
同时电影也是在晚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夜”这个词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一个人可能需要两种智慧,一种叫做白天的智慧,一种是晚上的智慧。龚自珍当年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就是说你在半夜里想到的事跟白天是不一样的。电影有的时候会突然让你很震动。毛尖当年给我推荐过一部电影,侯麦的《在莫德家的一夜》,特别简单的一个片子,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还没有碰触到它,你还要再看一遍。
毛尖刚才讲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什么样的人在今天值得信任?你会碰到一大堆意见,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广而告之,所有人都告诉你这个电影好,你会本能地想到一点,这些话都不可信。这个时候你最好身边有一个专家在。专家有的时候面目可憎,有的时候口味非常褊狭,比如他光喜欢哲学电影,那就麻烦了,他没办法喜欢北岛。而毛尖是什么电影都喜欢,她的价值观里面有“左翼”的东西,也有“右翼”的东西,也有极其个人主义的东西,非常宽泛,什么电影她都能欣赏。再有一个,她看的电影实在太多了。
她这本新书出版了,我有一个心愿,想看看最近毛尖又看了哪些东西。我看完以后还是非常震惊,因为它的兼容并包,而且都分析得非常透彻。她分析的不是叙述的故事、整个电影的场景,而是特别小的那些部分。我随手做了摘记,她这本书里有24部电影是我没有看过的,我都做了记号,打算回去看。因为她是值得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人非常宝贵,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本书。
后来心态放松下来,不再比武般地跟人谈电影慢慢获得了一种“向下超越”的力气
主持人:这本书的“后记”里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概意思是说,有时候看电影就像赌徒。你放在桌面上的赌注,可能是你生命中的两个小时,你不知道开出来的是好片还是烂片。赌徒的心态,反而让看烂片的过程变成更加有意思的生命历练。
毛尖老师刚才讲的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也许每个向往看更多艺术片或者更深奥电影的人都经历过,就是那些拼了命拿来的一个晦涩的电影,看不懂,怎么啃?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也开始狂热地看这些电影,有一天我电脑蓝屏了,然后我就使了个坏,告诉一个特别痴迷电影的朋友,说我搞到贾曼的《蓝》了。他就过来真的跟我一起看蓝屏看了十分钟。对于看这种片子的经验或者体验,毛老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毛尖:大学期间,因为格非老师的启蒙,在课堂上或通过私下传播的各种渠道,看了很多看不懂的电影。类似《去年在马里昂巴》这种,真的看了很多遍,又看小说又看电影,倍受打击。我在香港读书时,还见过罗伯格里耶,参加了他的讨论会。他带了自己的一些片子来,每天晚上在学校大教室放映,基本上每次放映结束,就剩下一两个人。说实话,我每次坚持在那里,也不过是自己一个傲娇的念头,至今我也不能说我真的看懂或者喜欢过他的哪部电影。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自己内心欲望饱满善于向外扩张的时期,总有一种向上超越的愿望。希望通过看特别难懂的、那种比自己高的、比自己的理念更抽象的文本,来达成一种向上超越。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也蛮重要的,因为它让你试图比自己更厉害一点。当时学术氛围中似乎也有一种比武的心态,朋友聊天,大家总试图说出一点特深刻、特陌生的观点。这种心态在当年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至少对于我,可能一直至今吧,还保持着比较旺盛的求知欲。
不过这个心态后来有很大改变。前几年,看到汪晖的文章《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他最后谈到一个概念是“向下超越”。那些欲望、生命中特别本能的直觉,之前我们希望抛开它们来达成更厉害的自我,但是通过阅读阿Q我们发现,这些很本能的东西表达着人生最真实的需求和关系,我们可以带着它们走,深化它们,穿越它们,藉此达成一种超越,这种叫向下超越。
我自觉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比如之前特别愿意看伯格曼,今天我们谈“恨过的导演”,伯格曼可以算一个。我跟他相处了非常长的时间,但其实我一直没完全进入。感觉我需要更多的生命经验才能理解《野草莓》《芬妮与亚历山大》和《假面》。另外一方面,前面讲了,在我自己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想向上超越。后来,我自己心态放松下来,不再比武般地跟人谈电影,我也慢慢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判断坐标,我重新发现好莱坞、重新审视类型片,重新在打打杀杀吃吃喝喝的电影中深化自己的美学感受,慢慢获得了一种“向下超越”的力气。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梦露,是一个环节。以前被人问到喜欢的演员或者导演之类的问题,都是欧洲脸,好像说好莱坞就不够高级。后来重新把梦露的电影全部看一遍,觉得在她的身上、脸上、她的表演中,童叟无欺有一种更感人、更伟大的东西在里面。
而到现在,我发现我喜欢的很多导演常有欧洲背景但转场好莱坞工作,像刘别谦、比利·怀德,还有希区柯克。这些导演,都在电影中实现了向下超越。
电影和文学最大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解释自己,解释自己的生存
主持人:格非老师,您那时候应该是看革命片、社会主义时期的电影吧?您是怎样理解和发现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的?这个对大家都是很重要的经验。
格非:一是伯格曼他们这批人都同属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包括电影、绘画、小说都是相通的。我们刚开始创作、写小说的时候,接受的全是现代主义的影响。那时候你要看一个懂的东西是会被人笑话的,一定要去看那些不懂的东西。读小说也是这样,一般大家都不屑于谈论能读懂的小说,一定是谈论那些读不懂的小说,在读不懂的小说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当然说句老实话,我们所谓读不懂的书,那些书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硬着头皮读一段时间,其实很容易就懂了,然后慢慢地有了这方面的积累。在电影、音乐等方面也是一样的,它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现代主义盛行的氛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发表了一些作品以后开始慢慢地跟一帮导演交往,包括张艺谋,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夏钢他们这些人,也使得我比较早地看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恐怕也是一个原因。我会到北京电影资料馆,就是小西天那里去看录像带,那种东西不是电影,而是特别好的、质量非常高的录像。有的时候也会放胶片。我记得当时看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是《呼喊与细雨》,1972年拍摄的彩色电影。看完之后觉得特别精彩,那个画面突然暗下去,一句话没有,一张脸浮现出来,然后那张脸迅速变红,银幕上模糊一片全是红色,然后那个红色又开始淡下去,浮现出来的又是一张脸。
当时觉得竟然还有人用特别“笨”的、话剧舞台的方法拍电影。那时候你看《毕业生》,看美国电影,你会发现伯格曼电影里面有特别简单的技术,就像小津安二郎所谓的固定机位——机位架在那里,人走来走去,他不会搞那些复杂的技巧。伯格曼也是如此,伯格曼的电影有话剧舞台的魅力,极其简单。我看《呼喊与细雨》时被震惊了,然后开始不断地搜罗他的片子看。
主持人:毛尖老师这本书也讲到所谓“不道德的电影”。为什么我们会痴迷于这些不道德的主题,比如犯罪的迷人之处?
毛尖:这是电影的本能,它并不真正召唤你犯罪,但是它把你心里的犯罪欲望释放出来。比如我们这一代,少年时候飞檐走壁的冲动,多少也是被电影缓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希区柯克为何有那么多观众,因为他永远在释放你邪恶的冲动。
格非:毛尖说的这些我是同意的。电影确实如此,小说也完全一样。你看现代小说,很少有现代小说把真善美作为主题来描写的,全是写恶的,甚至为恶这个事情加以阐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卡夫卡。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恶”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简单地从道德或非道德、善恶是非的角度来讨论。人在我看来有两个部分,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身上有上帝的一面,也有恶魔的一面。歌德早就说过这一点。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撕裂我们,它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呈现方式。
所以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无非是一种代偿的形式,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毛尖刚才说得很好,有的时候它是一种释放,你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你会突然非常放心,你会觉得自己很正常。否则的话这些欲望在你的体内,它没有办法跟基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解释自身。电影和文学最大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解释自己,解释自己的生存。
好的观众和好的读者永远比好的导演和好的小说家重要
主持人:刚才格非老师讲得特别重要,关于电影里面的这些世间种种,其实在帮助你定义自己内心深处不明所以的那些情绪、欲望,这时候你可能才更加确定自己的处境。
毛尖老师在《夜短梦长》这本书里面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消化电影的能力。作为一个观看者,有的时候看了一个片子,感觉它是好是坏,更大程度上在于观众能从中提取、消化、折射出什么。
毛尖: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试图和我以前写电影的方式有点不一样。《非常罪非常美》是我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读书时开始写的,那时候多少占着一点资讯比大陆读者多的优势,写作的时候也多少带点绍介的成分,常常会细致地讲述导演或演员的生平和花边,力图有趣生动,甚至妖娆,一边讲述他们电影的特殊性,一边呈现他们人生的花样性。我自己回头去看《非常罪非常美》,发现我选择的电影和电影人,都相对前卫或性格前卫。
写《夜短梦长》的时候,心态完全不一样。一方面,拜盗版和互联网所赐,中国电影观众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影观众,我们看的电影最多,种类最杂。我的阅片量不再是优势,所以我试图用电影来“写作”。李欧梵老师给我这本书写了序,他说我记性很好。其实根本不是我记性好,我讲电影情节的时候,回头把所有的电影都重新看过一遍,有些电影还看过好几遍。我写《白日美人》,德纳芙的每一个表情我都定格看过,把握住她的表情,我才能准确描述情节、准确表述她的心态。所以,写《夜短梦长》,我不再追求《非常罪非常美》时期的“性感”写法,我追求准确。
格非:从1988年跟毛尖认识一直到今天,在我的理解中,毛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通常人都不能兼美,有时候你有正义感可能没有趣味,可能你有趣味但是需要你严肃的时候又不够严肃。毛尖这两个部分都有。有的时候她会为某种价值辩护,当她为这种价值辩护的时候她不遗余力,会跟你较真儿。但有的时候她特别宽泛,什么电影都能看,不分电视、电影,港台片、狗血的东西,都有,这个太难得了。
电影文化是无限开阔的,我个人的看法,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好的观众和好的读者永远比好的导演和好的小说家重要,因为你没有好的观众不可能出现好的作品。大家对中国电影不满意,我觉得是中国的观众水平在下降。我说的是主体观众,他们太容易被资本控制,没有办法深思熟虑,没有办法建立关于电影史或者对电影的直觉。文学作品也一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慢慢地积累,也需要我们把视野开阔。
毛尖:本质上我是一个纵欲性人格,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不太讲道理,我以为这次我已经克制了。我接受格非老师对我的批评,对自己年轻时候喜欢过的导演、演员,以后还是要审慎。要准确,要更准确。
提问:我是大一学生,才19岁,人生经历很浅。想知道,毛尖老师看了这么多电影,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或者影响你哪些重大的决定?
毛尖: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肖申克的救赎》里看勇气,《怦然心动》里看初恋。
电影,当然对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当年不是上了格非老师的课,听了很多伯格曼,可能我就去攀登哲学高峰了。因为看了伯格曼,又去看了安东尼奥尼;因为安东尼奥尼,又去看了塔科夫斯基。这一层一层的关系和影响,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我。至今,不爽或者伤心,还是会看一部电影来排遣。
所以说,是电影把我领到了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包括我的很多人生判断,也常常跟电影有关。回望自己的看电影生涯,大概是,看过五千部电影后,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坐标;看过一万部以后,敢于对电影下判断,敢相对自信地说这部电影怎样怎样,就像我见过很多人以后对人性有了基本的判断。你现在那么年轻,根本不用着急,有大把时间可以看。
整理/雨驿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