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自由是我唯一的国度(4图)
发布时间:2018-04-22 13:40 | 来源:齐鲁晚报 2018-04-21 | 查看:5396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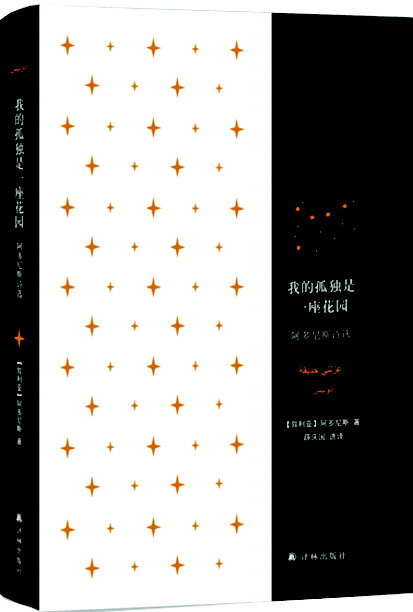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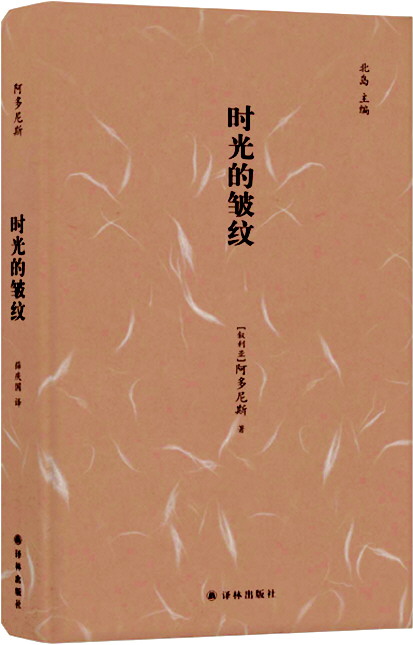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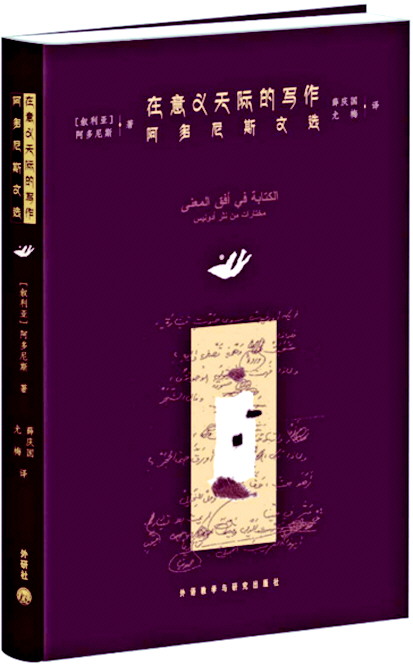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曲鹏
阿多尼斯去过很多地方,却始终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叙利亚。年近九旬的他坚持用阿拉伯语写作,在诗歌里歌颂阿拉伯语的美丽与阿拉伯世界曾经有过的辉煌,也向故土文化今天的堕落表示反抗。这位当今阿拉伯诗坛最负盛名的诗人,曾多次访问中国,他的《时光的皱纹》等中文版诗选也受到中国诗歌界的关注与认可。
阿多尼斯的一生都在漂泊和流亡,他生于叙利亚的卡宾萨,拥有黎巴嫩国籍,长期定居法国巴黎,他在诗中宣称自己只有一个国度——自由,“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在祖国和流亡地外,创造另一个所在
1930年阿多尼斯出生在叙利亚北部海边一个叫卡宾萨的小村庄。因为贫困,阿多尼斯到了13岁时还未上学,在家里帮父亲干活。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除了人人都需吟诵的《古兰经》,父亲也教他朗读阿拔斯王朝大诗人穆太奈比的诗歌。有一天,阿多尼斯做了一个梦。在梦中阿多尼斯作了首诗,献给叙利亚共和国的总统。
1944年,叙利亚经历了漫长的混乱,终于宣布独立。总统到阿多尼斯的家乡附近巡视。像梦境中一样,阿多尼斯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总统问: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阿多尼斯说:我想上学。总统当场允诺资助他去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学校念书——这个传奇般的经历改变了阿多尼斯的命运。
上中学时,他投向杂志的诗稿屡屡被退回,为了引起编辑的注意,他给自己起了源自古希腊神话的笔名——阿多尼斯。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一个每年死而复生、容颜不朽的美少年,热爱呼啸山林,即便是爱神维纳斯的追求也无法打动他。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好运,曾经被退回的稿件也纷纷被采用。
后来,阿多尼斯进入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叙利亚军队服役,一度投身左翼政治运动,并因此入狱6个月。这次入狱使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也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政治是诗歌眼里的草秸”。1956年退役后他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过国境线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一起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从此阿多尼斯在他的第一个流亡地黎巴嫩定居下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是阿拉伯世界中思想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阿多尼斯结交了诗人优素福·哈勒并创办了《诗歌》杂志,为那些不愿受陈规定律约束的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园地。他申请了黎巴嫩国籍,并获得了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出版了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四卷本,在阿拉伯文化界震惊四座。
1982年,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阿多尼斯与妻子再度流亡。最终,巴黎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流亡的驿站。
始终行走在流亡路上的阿多尼斯,诗歌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流亡。“流亡地不仅指空间,流亡地还存在于自身内,存在于语言中。”在阿多尼斯看来,流亡既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境遇,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隐喻。如何走出流亡地?他选择的方式是对自己所属的文化进行根本性质疑,成为这个文化的叛逆者和主动的流亡者,“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的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他要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
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
阿拉伯民族曾一度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诗歌闻名于世,诗歌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体现了阿拉伯民族文化的精髓。他们生来就是诗人,从诗歌作为起点看待神、看待人、看待事物,所以他们把人的存在转变为诗歌的存在。但一切都在变化,在阿多尼斯看来,阿拉伯人已经忘记自己的诗歌传统,融入到机械文化中。
上世纪60年代在贝鲁特创办刊物期间,阿多尼斯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书架一书架地看”,从中挑选出他心目中有价值、却遭到主流文学史忽略或贬低的诗歌,编纂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卷《阿拉伯诗歌选》。“你从中读到的不是权势,而是人;不是机构,而是个体;不是政治,而是自由;不是部落主义,而是叛逆;不是因袭者的修辞,而是创造者的体验。”
“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阿多尼斯试图重新定义和接续一个伟大的阿拉伯诗歌传统。1961年出版的《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是他形成自己独特诗歌风格的开始,对于所处的世界和自身的处境,发出了自己忠于真理的声音,突出展现了他叛逆传统的一面,被评论界定义为“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阿多尼斯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曾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被问及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诺奖”,这位年过八旬的诗人答道:“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都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阿多尼斯曾多次访问中国,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他的中国朋友、诗选中文译者薛庆国将他视作“阿拉伯世界的鲁迅”。他的四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包括三本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时光的皱纹》《我们身上爱的森林》和一本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我翻译成汉语的诗歌只占总数的3%—5%”。
在诗歌中寻找故乡,与现实反抗
到了西方之后,阿多尼斯开始对阿拉伯文化的处境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西方不仅不了解阿拉伯世界,而且还在歪曲阿拉伯世界。他们只愿意从宗教、教派、部落的层面去了解阿拉伯人,而不去了解阿拉伯世界进步、自由、主张真正对话的那些力量;他们甚至反对这样的力量。”
阿拉伯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当代阿拉伯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阿多尼斯眼中的阿拉伯现状却与之相反:“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他这样描述阿拉伯民族的生存现状,“尽管今天阿拉伯人的现状不是游牧而是定居,不是骆驼而是汽车,不是沙漠而是城市,可是他们冲动地思考和行动,似乎依旧在过着游牧生活……你走进任何一个阿拉伯城市,用文明开化的标准衡量它,就会发现它近乎沙漠。”
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落后现状,阿多尼斯追求变革与突破,但对于通过政权更迭来改变社会不抱希望,反而对通过文艺尤其是诗歌来促进社会变革有着传教士般的信念和执着——这种方式虽然柔和,但潜移默化中影响更为深远。不同的诗歌呈现了不同的情感,如果用一种情感来形容阿多尼斯所有的诗歌,他个人认为“愤怒”这个词最为恰当,“正因为愤怒,才产生重建世界的愿望,诗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改变世界的形象”。
阿多尼斯定居法国多年,虽深谙法语,却只用阿拉伯语创作诗歌。“自由地表达,才是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阿拉伯语。因为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我才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感受到我作为人的价值。”然而,令阿多尼斯感到失望的是,“今天几乎找不出一个读者,能说一口完美无缺的阿拉伯语,甚至你拿一篇文章让他读,读得完全没有错误,也找不出。”更令人不安的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很多危险,“一个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了解的人,怎么能指望他了解其他事物”。他坚持用母语写作,是为了向阿拉伯语的美丽与曾经有过的辉煌表示忠诚,也为了向阿拉伯文化今天的堕落表示反抗。
【阿多尼斯诗选】
◎对话
——“你是谁?你要选择谁,米赫亚尔?
你朝向何方——上帝,或魔鬼的深渊?
深渊远去,深渊又回来,
世界就是选择。”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魔鬼,
两者都是墙,
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觉者的困惑……”
◎祖国
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
我折腰;为洒落着被我遗忘的泪水的小径
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
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
我折腰;为被售卖、
在祷告、在擦皮鞋的孩子
(在我的国家,我们都祷告,都擦皮鞋)
为那块我忍着饥馑
刻下“它是我眼皮下滚动的雨和闪电”的岩石
为我颠沛失落中把它的土揣在怀里的家园
我折腰——
所有这一切,才是我的祖国,而不是大马士革。
◎水的肝脏
雨色朦胧,然而
自有青草懂得雨的言语
领会雨的节奏和秘密
那么,为什么
在我们历史的源泉里,连水的肝脏也长了肿瘤?
◎歌咏
我看到叙利亚的悲伤,正捧着竖琴
唱起无声的歌咏
(选自《时光的皱纹》,译者薛国庆)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