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旧民间救助艾滋病组织:让病人“漂漂亮亮”地走(9图)
发布时间:2013-12-13 10:59 | 来源:南都网 2013-04-19 08:57:41 | 查看:9732次
摘要:个旧的资源枯竭,由此产生的大量失去生计的工人成为毒品和疾病的主要受虐者。至2010年,个旧已成为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除了政府在行动,个旧艾滋病人群体也起来自救。除了治病和生存,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的回归。
1980年代,靠近云南南部边境的个旧市便开始受到毒品的侵扰,艾滋病也在1990年代中期紧跟而至。至2010年,个旧已成为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而个旧的资源枯竭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产生的大量失去生计的产业工人成为毒品和疾病的主要受虐者。一项媒体报道的数字是,在人口40万的个旧,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至少7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当地政府进行大规模筛查,干预控制艾滋病。同年,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在这里启动。“出乎预料的高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如此评价。
民间也没有坐等。2005年起,个旧陆续成立了十余家艾滋病预防、关怀民间组织,其中有些是艾滋病感染者自发组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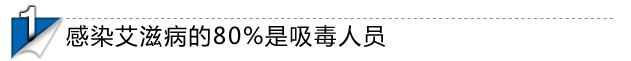
在当地卫生系统,曾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0个被感染的,其中80%是吸毒人员。”救助吸毒人员,成为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
2004年4月,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启动。仅第一个月,治疗点便接纳超过80名病人且无一人脱离治疗。美沙酮是一种毒品替代物,也是国家严格控制的鸦片类麻醉药品,流到黑市上便成了毒品。
治疗中心主任闵向东2005年对来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在呼吁要为吸毒者公开提供一种替代药物,以阻断他们共用注射器吸毒的行为。”
到2010年,个旧市已有2家美沙酮门诊以及4个拓展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人员累计已达1000余人,管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59人,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144人。
大多数吸毒者感染艾滋病都是由于共用针具,交换针具,就成了个旧卫生部门的另一项举措。从2004年开始,云南个旧的吸毒人员便可以在当地的艾滋病咨询中心免费领取到清洁的针具,用于静脉注射吸毒。
开展交换针具的初期,也曾发生过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工作方针的矛盾。有的吸毒者刚交换完针具出去就被公安人员抓走,针具交换处一度门可罗雀。
在多方协调下,公安部门改变了方法,尝试去配合卫生部门的新举措。“我们要看看这种做法的效果到底如何。”一位警察学院负责人说。
直到现在,无论是美沙酮治疗还是针具交换都仍旧存在着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前者被认为是主动提供毒品,后者则被称作是在默许吸毒。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方法遭到很多国家的禁止。
但对于个旧来讲,也许别无选择。闵向东介绍,开展这两项工作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戒毒,而是为了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个旧这个出于现实考虑、在争议中前行的做法最终获得回报。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9个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下降了5.8%,而在没有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52个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却上升了5.9%.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顾问夏国美女士对此评价称,“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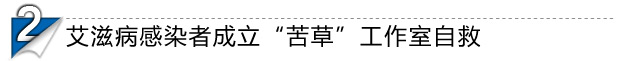
很多所谓的按摩房、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当地人知道,这都是“红灯区”。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性工作者匆匆在巷口照镜子。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来自贵州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里整理头发。据调查,这样的 性工作者在工人村社区。(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个旧的老火车站周边,有许多小KTV厅,也是当地的“红灯区”之一。(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在个旧官方采取种种举措对抗艾滋病的蔓延时,民间也组织起来开始自救,其中还包括不少艾滋病感染者。
2005年,艾滋病感染者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服务人群与工作人员均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与“苦草”同一时间成立的还有十余家防艾民间组织,如关注吸毒者的“胡杨树”,重视社区预防与关怀的“葵花园”等。他们更多地关注政府照顾不到的领域,如对性工作者的预防培训以及生产自救。
成立之初,“苦草”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向性工作者们普及防护知识避免交叉感染,“要让大家活下来”。此前由于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后便放弃了预防措施。李曼便曾见到一位苦草成员因为一直进行无保护性交易,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并最终死亡。
几乎每个月“苦草”都会举办阳性预防的相关培训活动。因为频繁地有陌生人员出入,还曾有邻居打110举报“苦草”工作室说看到有一群“小姐”在聚众吸毒。
2009年,“苦草”工作室进行了一次针对性工作者常客的调查。结果发现,80名常客中,只有6名是艾滋病感染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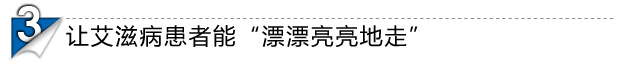
活下去之后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
2008年,“苦草”工作室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起名为“芳草”,意思是苦尽甘来。
洗一次车要1个小时,收入仅有10块钱。但让李曼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成员都抢着想到洗车场工作,“来不了的还一直在抱怨”。最终洗车场让8名“苦草”成员告别了性工作。
“从来没挣过那么干净的钱。”杨慧在回忆洗车场生活时说。
随着工作的开展,“苦草”工作室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断有“姐妹”慕名加入。到2012年,“苦草”工作室已有注册成员276人,全部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
出于吸毒者对自身身份的顾虑,许多人不敢去卫生部门交换针具,他们更愿意相信“胡杨树”这样的民间组织。“可能是因为同为吸毒者的关系吧。”胡杨树负责人辛德明说。
在民间组织活跃时期,有时候到了周末甚至会出现几家同时举办活动争抢成员的场景。“我们一下成了宝贝。”艾滋病感染者张琴说。
但与政府部门一样,民间组织也面临着种种难题。进入2010年后,由于国际基金组织的撤离,大多数民间组织陷入了资金紧张的困境。“苦草”工作室的阳性预防工作便不得不停止,“胡杨树”的吸毒人员走访也已暂停了很长时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才能救更多的人。”辛德明说。
经费紧张的同时,大批个旧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进入发病期,临终关怀成了各家民间组织的主要工作。
从2006年到2013年,“苦草”共送走48名成员。为让成员们能“漂漂亮亮”地走,李曼学会了遗体美容,还坚持每次都让尽可能多的成员参加送别。
这多少让其他人感到了一丝宽慰。“自己死后要是也有这么多人送别,那就不怕了。”张琴在回忆为成员送别的场景时说。
如今死亡不断降临,但对于李曼和更多的个旧病人来说,恢复生而为人的尊严才是他们更大的渴望。
“即使病了,我们也是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人。”
(责任编辑:杨晓均)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